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并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7.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5.3万亿美元的规模。这既得益于数字经济本身技术周期短、产业迭代快、更有利于后来者追赶的特性,也得益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不断成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同时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政府对数字经济审慎包容的监管方针密切相关,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紧紧抓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在巩固我国数字产业化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才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塑造实体经济新动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加快创新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数据要素在创新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数据要素具有内生增长、低边际成本、易复制、非损耗等特点,能够克服传统要素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加大创新的要素供给。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还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深化市场分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组织,提升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效率和创新能力。
下一步,应着力解决数据难以确定产权、难以定价、难以交易等问题,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建设,探索将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开,并运用区块链、隐私计算、数据沙箱等技术,解决数据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促进数据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积极推动数据和知识软件化、系统化、平台化,提升数据要素服务能力。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在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结构上的积极作用
提振消费是今年的优先工作。数字经济通过平台经济、网络零售等新业态改变了消费形态,扩大了消费需求,提高了交易匹配效率,并进一步通过消费方式变革推动了生产方式由“标准+集中”式的工业化大生产向“定制+分布”式的数字化柔性生产体系转变。
数字技术还将教育、医疗等部分“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变得“可贸易”,扩大了服务消费的规模和范围。下一步,应强化数字经济对传统消费业态、场景的创新带动能力,并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
水平动态平衡。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接入主体越多收益越大。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者,但在生产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很低,“转不起、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下一阶段,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网络效应的重点是扩大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广度”。一是要深化“因业施策”,找准产业和企业的痛点,“由易到难”推动数字化转型,切实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二是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支持门槛低、易部署的小程序,云化SaaS软件等“轻量应用”“微服务”提供者,以创新券和税收抵扣、研发加计扣除等形式,帮助企业加快迈出数字化转型第一步。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着眼于以“出海”强化国际竞争力
我国在部分数字经济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发达国家仍占据技术的制高点。
下一步,在产品和服务出海的基础上,还应加强资本出海、技术出海,通过收并购先进企业和技术、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引进或在当地雇用人才等多种方式,广泛汇聚全球优秀人才和技术,不断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维护产业安全、数据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数字经济的“卡脖子”往往并不是因为国内没有可供国产替代的产品,而是由于产品和技术不成熟,市场规模较小,反过来削弱了进一步技术迭代的应用基础和持续投入的财务基础,形成恶性循环。
破解“卡脖子”难题,关键是通过政府采购或制定相应的数据收集、存储和安全规则等措施,扩大国产产品的市场份额,尽快实现“使用—反馈—提升技术—扩大市场”的良性循环。
数据要素内生且近乎无限增长的特性和资本增值相结合,可能会催生更具风险的金融产品甚至金融“寡头”。因此,在发挥金融科技对降低交易成本,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周转效率的优势的基础上,更要明确将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科技的资格审查和数据监管,强化金融机构竞争,并鼓励龙头企业等参与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信用贷、订单贷等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唯有更好地认识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坚持自立自强,方能更好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勇立潮头,在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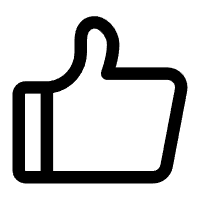 点赞:
点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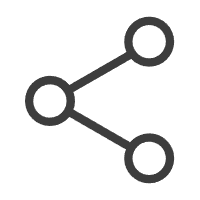 分享
分享

 服务
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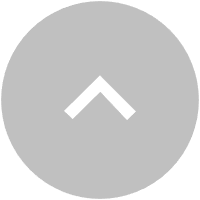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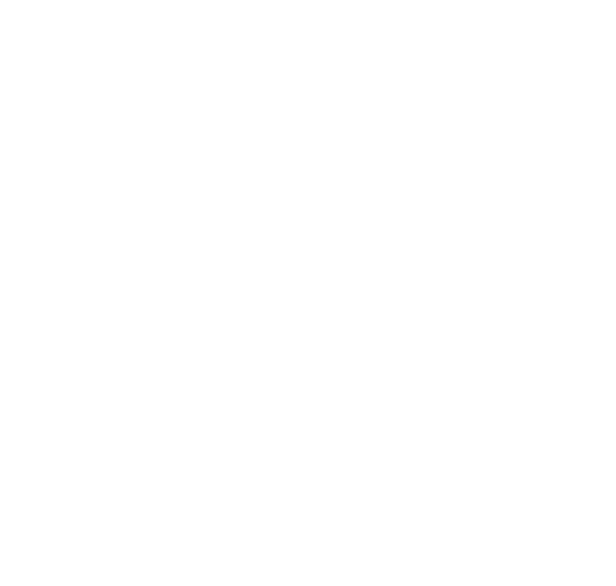 请点击右上角分享给微信朋友或朋友圈
请点击右上角分享给微信朋友或朋友圈


